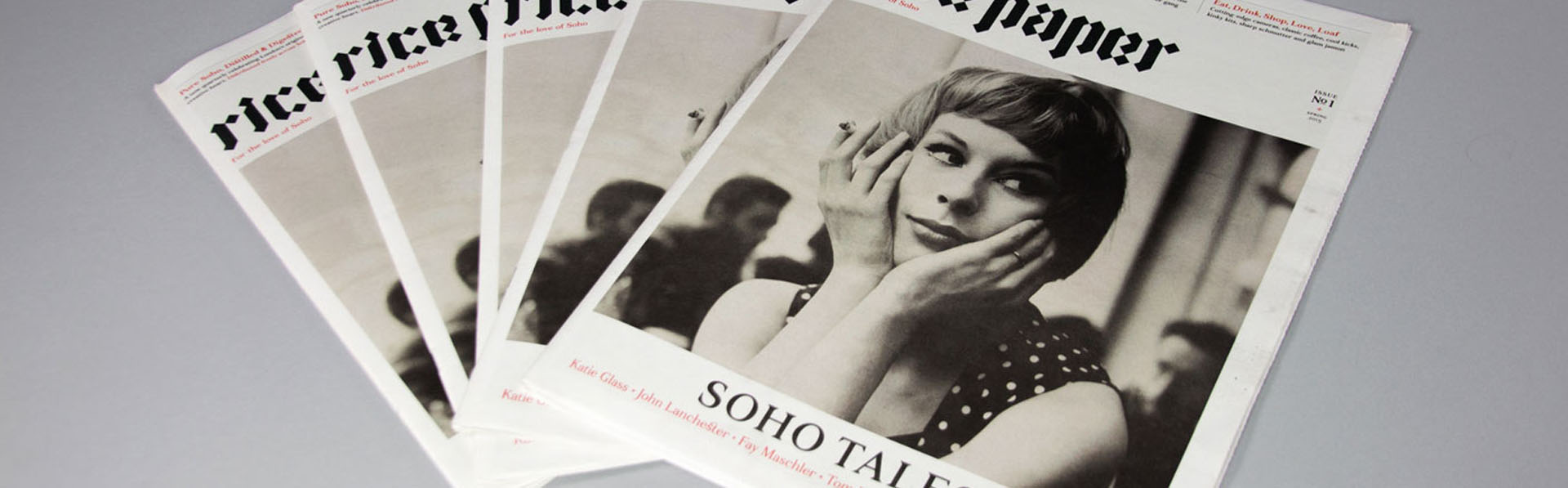2025年农历新年前夕,品牌方再次掀起春节营销的符号狂欢。尽管互联网、食品饮料、3C数码等不同领域纷纷推出不同主题的营销活动,但其核心依然是相似的——通常情况下,营销重点均围绕春节习俗(如扫尘、贴年红、吃年夜饭、拜年等)以及情感话题(如归家、团圆、新年愿望等)展开[1]。从康巴丝赞助春晚零点报时钟声到集支付宝福卡,从伊利百搭到汇源申遗广告,商业力量正通过具象化的物,深度介入到人们的集体记忆构建场域中。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性地将记忆研究纳入社会学范畴中,认为人们是根据既定的社会框架来建构“过去”的,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共享“过去”的过程和结果[2]。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些话题都涉及到通过产品这一“物”来连接人与人、人与地域的集体记忆。那么,品牌方是如何借助与春节相关的“物”及其本体唤起用户集体记忆的?人们如何参与记忆文本的阐释、构造和流通?当具有消费属性的“物”深度融入人们情感最为浓烈的时刻,这些“物”又是否会重构人们的集体记忆?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标识性的传统节日,蕴含着华夏儿女深沉的集体记忆。每年例行的春节庙会等民俗活动和春晚等文化盛事是集体记忆重现的天然载体。在重现集体记忆这一进程中,品牌广告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5年春节前夕,伊利与贾冰携手打造的春节广告,以“过年好搭子”为主题,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探讨当代青年的内心困惑与生活境遇,巧妙地将抽象的趣味性与春节传统相融合。类似的品牌广告不仅强化了春节的集体记忆,更凭借创新性的表达勾连起品牌方与春节这一节点。
节日消费的背后是记忆符号的循环再生产,物的意义生成依赖于现有的文化系统。贺岁广告中的伴手礼、生肖吉祥物等记忆容器,本质是品牌对传统符号的二次编码。如汇源果汁借申遗成功广告将饮品转化为文化使者;康巴丝通过8年零点报时将钟表转译为时间仪式道具。
在贺岁广告中,品牌方常通过锚定文化原型、激活感官以唤起情感、深度绑定春节象征意义三种策略将普通商品转化为记忆符号。奥利奥连续多年推出的春节限定产品,从龙年DIY灯笼礼盒到印有“福、禄、寿、喜、财”的春节限定饼纹,将零食包装迭代为微型非遗展。这种呈现策略实则是布迪厄象征资本的具象化——当消费者咀嚼饼干时,也在无意识中完成文化PG电子模拟器 PG电子网站身份的咀嚼。
可以说,春节营销中的“物”(如年货、礼品等)不仅是节日庆祝的物质载体,也是集体记忆的象征。通过消费这些“物”,人们不仅满足了节日的需求,也在无形中捡拾了集体记忆。
回想十余年前的春节——放鞭炮、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整点倒数并互道新年快乐是常见光景。如今,当腊月梅香飘散于街头,成千上万的用户不约而同地打开手机镜头捕捉福字,一场名为“集五福”的横跨虚拟与现实的数字狂欢便拉开帷幕。这款简单的社交互动项目已历经八载春秋,蜕变为数字时代的全民新年俗,在当代中国人的春节记忆中刻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支付宝集五福活动自2016年诞生以来,以科技赋能传统年俗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新诠释了春节的文化内涵。以新媒体的方式为大众带来颇具趣味与互动感的“新年俗”,让快节奏社会下的大众感受了一把属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年欢乐。如今,支付宝的“集五福”已成为了新时代的“春晚”盛事。当除夕夜的钟声敲响,千家万户手机屏幕上跃动的福卡与电视里的春晚交相辉映,构成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奇妙图景。
原子化社会映射的是碎片化的社交和微粒化的个体,而集五福等数字年俗的兴起,恰如其分地映射出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配。记忆的存续不仅依赖认知,更需要通过身体行为的重复操演,实现代际传递[3]。在原子化社会关系与快节奏生活消解传统邻里亲缘的当下,集五福活动通过社交裂变重构了情感联结的数字化场景:亲友间互换福卡的温情互动,同事群中求敬业福的嬉笑调侃,乃至陌生人之间的福气传递,都在虚拟空间织就了一张新型社交网络,让年味在云端持续发酵,也让春节记忆一代代传承下来。
“结构-权力”和“文化-认同”是学界普遍用于研究集体记忆的两个范式,记忆的建构往往兼具“结构的”和“文化的”向度[4]。如果说上文侧重谈论的是“文化-认同”的向度,下文则从“结构-权力”维度考量品牌背后蕴含的商业化力量如何深层影响人们的认同。
尽管某品牌在2008年赞助北京奥运会时推出的广告曾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极具洗脑效果的重复轰炸式广告,至今仍是人们在讨论奥运会广告乃至奥运会时无法绕开的话题。以“归家”“火车”“送礼”等标签凸显春节的典型意象,是大众传媒建构话语共通性,进行记忆实践的重要方式。春节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并非仅源于官方力量的推动以及代际相传的延续,品牌方推出的新春广告从大众传媒的角度为集体记忆的构建增添了中间态。
当前,品牌方频频借助春节TVC耦合品牌与春节记忆,并为此开展了多样化的表达实践,构建起“品牌广告 - 大众传媒 - 集体记忆”的互动模式。2025年春节,剑南春打造家国同春主题集市,实则是将消费空间转化为记忆剧场,通过专业认证(CCTV报道)+模范话语(非遗传承人背书)完成记忆加冕。
但如今商业力量的记忆书写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大量传统文化捍卫者认为过度商业化的伪年俗稀释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集体记忆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建构之余,泛化是其必经阶段。代际认知断层带来个体对典型意象的认知弱化。正如美国学者施瓦茨检验的集体记忆的“现实中心论”一般,其在研究几代美国人对林肯的记忆时发现代际传承形成了一个话语共生环,即林肯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在代际间得到了相对完整的传承,但每一代人心中又各有不同的林肯[5]。与无数社媒评论遥相呼应,Z世代对火车归家等广告的共情度较80后、90后均有所下降,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面临泛化困境。
从唤醒传统到建构新俗,再到重构代际认同,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位置,尤其是互联网使集体记忆的传播手段、途径和影响力都产生了巨大变化[6]。
从康巴丝钟声到元宇宙庙会,春节广告中的物正在构建记忆的平行宇宙。它们既是哈布瓦赫笔下的记忆社会框架,也是德波警示的景观社会产物。当品牌成为记忆工程师,我们需要警惕文化空心化,但更应看到: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商业力量或许正在创造集体记忆的新型保存方式——不是刻在石碑上,而是活在每一次扫福卡的手指滑动间,存于每个拆开新年盲盒礼包的期待中。
[2]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J].国际新闻界,2020,42(01):154-176.
[4]陈旭光.角色模范与集体记忆:体育传播中的“郎平话语”研究[J].体育与科学,2021,42(06):50-60.